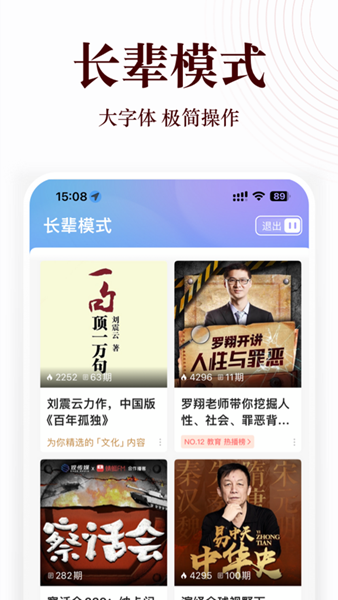蜗居:宋思明在海藻洗澡时故意接电话的举动,说透他的算计有多狠
注|原著与电视剧有出入
对于宋思明而言,从来都是得不到的最好。

宋思明试图把海藻的存在当成曾经白月光的替代品。
但白月光如果能够被替代,那还叫白月光吗?
宋思明走在路上,月光拨开层层迷雾照亮了他,可月亮却从未奔他而来。
电影《龙凤配》中,有这样一句台词:
可是月亮奔我而来的话,那还算什么月亮,我不要,我要让它永远清冷皎洁,永远都在天穹高悬。

永怀感念和敬畏,与伸手触碰抚摸的感受,永远都不一样。
从前,苏惠在宋思明的心中是留存完整,保留了二十年之久的白月光;可现在,宋思明的举动,却只剩了玷污。
而她的存在,也成为了宋思明宣泄自身欲望和私心的一个借口。
从他对海藻动了念头,心头贪恋的却是白月光的那一刻起,就注定要为自己的贪心付出代价。

红玫瑰与白玫瑰
宋思明最开始注意到海藻,是因为对方像他年轻时候的白月光。

可悲的是:
他从未真正得到过曾经的白月光。
从幻想得到,再到真正得到自己的“白月光”,宋思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。
然而:
白月光如果能被得到,能拿来成为他的情人,他还会如此沉迷吗?
对方在最美好的年华中逝去,在少年的心头留下了最深的眷恋与烙印,而自己那时候却正是最无能为力的年纪,又如何不刻骨铭心呢?

很多时候,我们走入的往往是另一种歧途,或者可以说,我们走入的,是自己所创造的迷途,宋思明亦是如此。
但宋思明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。
有些东西,在他的心头,其实就是永远放不下的。
譬如今日的海藻,又譬如昨日的白月光苏惠,其实他心里都念着。
一个是镌刻在心头二十多年,挂在众人心目中的白月光;另一个则是带给自己鱼水欢愉,时时围绕在自己心头的朱砂痣。

其实真的很难选。
他不是看不透,只是有些东西,看透了却未必一定能够接受。
其实并不是得不到的最好,而是得不到的,却还心心念念的感觉最好。
而是萦绕在心头二十多年来对自己的压抑,对内心欲望的压抑,造就了他在走向海藻的同时,也把他自己的一生给断送了。
在海藻出现之前,宋思明甚至可以说从未有过软肋,他时刻警惕着,注重着身边的威胁,在人人口中的风评都很好,直到海藻的出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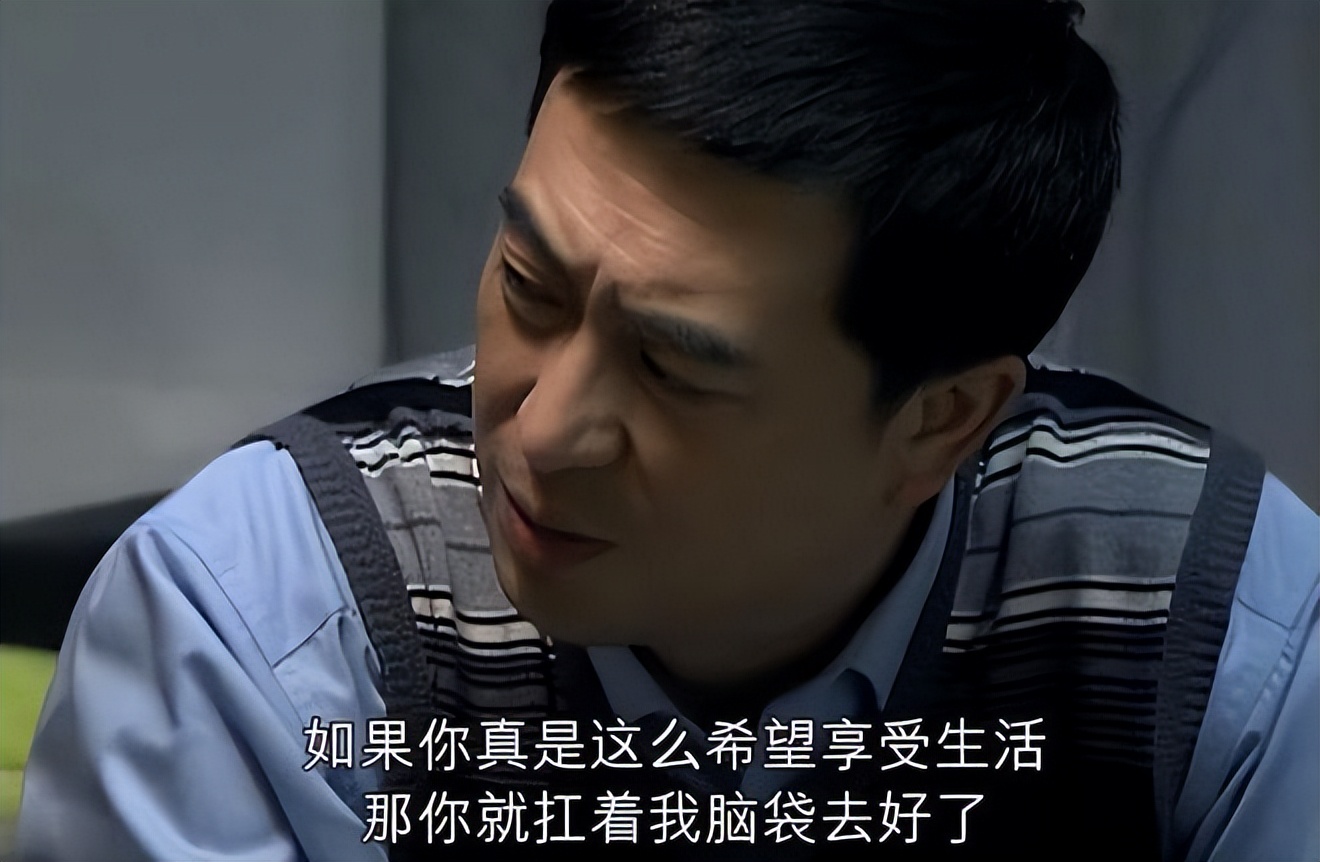
就连他自己都说,海藻是自己的软肋。
其实这二十年来,宋思明不是没有机会完成自己这二十年来的遗憾。
但他并没有选择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,给自己松懈的借口,给自己弥补遗憾的机会。
一是当时自己家庭的状况不允许,另一方面,则是他一直没有等到一个契机——一个可以放纵欲望的契机。
他自己也在心底承认:
如果自己不是为了往上爬,而选择了妻子的话,恐怕他未必能到今天这个位置。

说到底:
海藻的到来,只是为宋思明宣泄内心压抑的欲望和私心,找到了一个借口。
甚至可以说,是一个契机,就像海藻母亲说的,海藻只是刚好撞进了宋思明的眼里,就算没有海藻,也会有水草,珊瑚。
当一个人拥有的过多,却认为这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时候,那他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——成功的背后,往往伴随着运气的扶助,天底下没有绝对的能力,也没有绝对的幸运。
何况,多年来宋思明的自尊,已经变了性质,成为了自傲。

宋思明不是不清楚,对方的出现,是陈寺福讨好自己的陷阱。
但他自信到,觉得自己可以在掌控之内,选择自己的能力,但往往自信过度,就成了自大。
试问白月光与朱砂痣,究竟哪个留在自己心头的烙印更深呢?
张爱玲曾就这个问题做出了解答:
“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,至少两个。 娶了红玫瑰,久而久之,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,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,娶了白玫瑰,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,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。 ”

无论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,在未曾得到之前,我们所追求的,是得到之时的虚荣感,是得到之时的快感与胜利;但得到之后,就未必了。
人总是喜欢喜新厌旧,也是这个道理,而得到与得不到的感觉,终究是不一样的。
饭粘子与蚊子血
白月光与朱砂痣的讨论,无论是放在从前还是现在,都是经久不衰的热议话题。

可无论是白月光还是朱砂痣,在得到之后的结局,都会成为饭粘子和蚊子血。
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。
没有得到的时候,千好万好,千求万求,一派忠心耿耿,非卿不娶的模样;得到之后,便开始处处挑剔,不再珍惜,仿佛从前那个苦苦哀求的人,不是自己似的。
便如宋思明主动暴露自己的出轨一样。
宋思明带着海藻去同学会,并不是为了顾及老同学们所谓的安全感,其实更多的,则是为了满足众人的目光望向自己的虚荣感。

甚至可以说,他享受这种感觉,享受这种被众人环绕,享受自己目前所拥有的权力之下,所包裹的要风得风,要雨得雨的这种感觉。
为什么之前大多数人所偏爱的,都是咸鱼翻身,底层打拼逆袭成功的剧情?
正是因为,这是大众所偏好的爽点:
在翻身逆袭之后的打脸剧情,草根出身,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等一系列数不胜数的例子,大家所坚信的,都是命运的改变,是命运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。
或者更通俗点说,是“不蒸馒头争口气”的坚持。

而宋思明喜欢,也正是这样的感觉。
他带海藻来到宴会上,感如此高调不避嫌,就是为了向众人昭示一个讯号:
看,我再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穷小子了,我如今拥有着超然的社会地位,有着大量的财富却深藏不露的权势,更找到了当年白月光的“替代者”,我完成了自己的逆袭人生。
说到底,他如此高调,就是为了昭示自己如今所拥有的一切,向如今的自己,或者说向过去二十年前的那个自己,说明一件事:
如今,我也拥有了自己的璀璨,而得到这一切,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。

张爱玲在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中写道:
振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,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,一个是他的红玫瑰。 一个是圣洁的妻,一个是热烈的情妇——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。
而宋思明对妻子和情人泾渭分明的态度,则恰好说明了这句话的真实性。
在海藻彻底来到他的身边后,海藻曾讨好性地给他做了一顿饭,他却在海藻做好饭讨好他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:
“这些不是你应该做的。”

言下之意,宋思明其实早已将妻子和情人的职能分配的清清楚楚。
在宋思明的心里,妻子就应该是安定家庭大后方的主力,但情人却只需要做好讨好自己,提供情欲的职责就行了。
但讽刺的是:
若是没有妻子这些年的扶助和大后方的安定,他又怎么会这么快到今天的位置?
其实一切的真相,他早已向大众展示的清清楚楚。

“一个男人,一生总要有一辆好车、若干知己,和......否则这一生多失败。”
“人的肉体和精神是可分的。你即便在精神上很爱一个人,肉体却不会忠于他。肉体是很无耻很无耻的贪婪,在贪婪的肉体面前,精神会显得很渺小。”
在同学聚会后,他借着老同学妻子的口散播出自己出轨的既定事实,其实就是在逼着对方接受这个结果。
一方面是自己如今在工作上的羽翼已成,另一方面,也是因为在那个圈子里,他被同化了。
带着海藻去聚会,其实在一定程度就已经表明,宋思明已然接受了这个圈子里的既定事实。

说到底,宋思明不过是个再典型不过的普通人,甚至可以说,他是个放纵自己欲望的,没有那么强自控力(后期)的人。
他只爱他自己,作为一个男人,他既没有那么坚贞,也没有那么凉薄,只是他难以两边都舍弃,两边都想好,两边都想要。
欲望与私心
书里,在欲望的驱使下,宋思明对海藻的私心愈发展露无疑。

在海藻洗澡的时候,宋思明曾擅自接过她的电话,而不幸的是,这电话正是小贝打来的。
电话挂后,宋思明询问海藻:
“海藻,难道你打算就这么继续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徘徊下去?”
可宋思明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妻子和海藻之间徘徊呢?
在同学聚会的酒店里,宋思明质询海藻的犹豫徘徊,明显是逼着她在两个人之间做选择,可他自己难道就没有在“既要又要”吗?

当时海藻已然在解决了海萍的燃眉之急后,有了脱离宋思明的想法。
可宋思明又是什么人?如果没有收获,他又如何肯付出呢?
归根结底,他始终是一个算计至深,自私至深的人,而很多时候,人性从来都不可试探。
在宾馆的时候,他对着海藻深情告白:
“海藻,我很珍惜你,我知道我很鲁莽,将你的第一次拿去。但你要相信我,我并不像许多男人那样,只对情人逢场作戏。我把你当我心头的珍珠,和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。我要对你负担起责任,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义务。你知道吗?我这一生,从不请求别人,但我很认真地请求你,做我的爱人。陪伴我,和我在一起。”

可海藻并非是他心头所想的那般清纯可爱,纯洁无暇。
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,本质上,宋思明和海藻时一类人,他们都是那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而选择互相遮掩隐瞒,自欺欺人的人。
宋思明说自己喜欢海藻,可他那是真的爱海藻吗?真的爱海藻,他又如何忍心让对方成为社会的硕鼠,成为人人唾弃的第三者?
何况,宋思明的最开始喜欢海藻,也不过是因为她长的像自己的白月光而已,他真正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时,是在满足自我畅想,觉得海藻时他的第一个女人的时候。

但可悲的是,自始至终,一切都是他的自我想象而已,若是得知真相,他还会把海藻当成自己心头的珍珠吗?
恐怕到最后,海藻真的会成为他的一枚棋子,真的成了他口中“逢场作戏”的一个工具罢了。
而海藻也说自己喜欢宋思明,可那又是真正的喜欢吗?
海藻的物欲和情欲同样也一直被压抑着,无论是在物质上的还是情感上,其实海藻比她自己想象中的,要得更多。

只不过,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展现自己自我压抑的生活。
而她自己,也一直在自我压抑着,而碰上宋思明,海藻的欲望被他的手段打开了,或者说她心中一直被压抑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而已。
说到底,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,遇上了一个年轻蓬勃了却物欲丰满的女人,多年来的物欲压抑和情欲上的压抑,让这两个人一拍即合,他们其实心底都明白,自己不过是在自欺欺人,是在互相满足对方罢了。
最后的结局,其实已然说明了这两个人贪心的人,为自己的贪婪和虚荣所付出代价。

“切!二奶哪能算女人?硕鼠!社会的硕鼠!她自己不给别人活路。早干吗去了?”
“你们都别吵!这是病人!是需要我们照顾料理的病人!你管人家做什么的干吗?你们说来说去,都没说到点子上。谁是罪魁祸首?那个男人!那个男人!该死的是那个男人!可怜了活活一条小命。造孽!”
那个该死的男人,已经死了。正躺在停尸房。

作者:花语迟,自由撰稿人,兼具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,专注女性成长与情感方面的写作,励志做一个努力写作,热爱阅读的女子。
热爱文字之美,卖字为生,相信有一天能成就更好的自己。